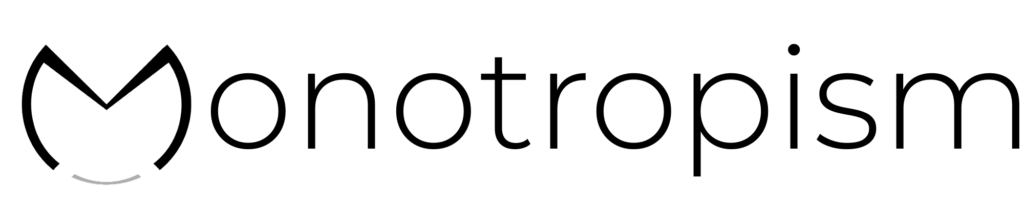作者 :黛娜·KC·默里
出现在Ed Murray,Coming Out Asperger:Diagnostic, Disclosure and Self-confidence (2005),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伦敦。
几年来,我一直在试探性地向我越来越多的自闭症朋友检查/披露我自己可能属于自闭症谱系某处的可能性,并且我对几乎普遍接受感到荣幸。 然而,我并不完全认为我配得上这个荣誉是有原因的:我是灵活的,甚至是滑溜溜的;我是灵活的,甚至是滑溜的。我以总体上有充分理由的信心,冷静地行事。我是可以接受的。 几年前,Jane Meyerding从在线小组ANI-L(www.ani.ac)中发现了一个对我有用的类别,“自闭症表亲”。 她还告诉我一个故事,关于如何成为贵格会教徒,因此和平主义者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寻求关于继续携带剑的建议,作为一名男性贵族,他以前一直这样做。 他被告知他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戴剑,也就是说,只要他的良心允许他。 因此,我已经将我的高AQ分数透露给我的主要职业自闭症论坛1;我用它来向我的朋友表明,我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要奇怪一些。我的丈夫和儿子早先有暗示,似乎不受干扰。 现在我是第一次进入印刷,现在我已经摘下了剑,我会不会更直接地变得脆弱,不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以下是我对我的生活所做的叙述。 我把它变成说明一个论点的方式。 这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同样真实。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在阅读它时一直在想,“等等! 那可能是我…“ – 想想! 也许你的生活也可以这样讲述?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在Kanner和Asperger首次发表后不久长大的人,她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来表达她的意思,他的自我技能的展示几乎总是足够的,直到今天,她总是得到她需要的所有支持。 这是一个关于如果你擅长社会喜欢的东西,那么远离麻烦是多么容易的故事,以及它如何产生建立信心的连锁反应,即对自我效能感的积极期望,没有它,探索和发现的潜力可能会削弱。 它还表明,即使是在某些领域有巨大信心的人,也会在情绪崩溃的状态下,通过微小的明显触发因素而全面失去信心。 在那些罕见的情况下,当她的意义被误解或不被理解,假设的顺利相遇被不匹配的期望和消极的假设所吞没时,她可能会成为一个无法沟通,社交,思考的人 – 并且被强烈吸引,永远不会再让自己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中。
黛娜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患有自闭症,他们告诉她,他们认为她是“其中之一”;这同样适用于她的普通朋友。 大多数时候,她都聚集在任何一个营地。 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她在Baron-Cohen客厅游戏上的分数中,该游戏用于识别一个人对各种相关特征的立场,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男性大脑”还是自闭症谱系疾病的诊断。 在AQ测试中,(“自闭症商数”)SQ测试(“系统化商数”)和EQ测试(“移情商数”),她在典型男性和可能患有自闭症谱系诊断的人之间得分[ref]。 她还在托尼·阿特伍德(Tony Attwood)关于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书中的简短问卷中回顾性地获得了亚临床水平的分数[ ref]。 (为了更好地衡量,她的无名指也比食指长[ref],这显然是男性和自闭症倾向的另一个迹象。
与这些迹象相反,她在剩余的Baron-Cohen测试中得分处于正常范围的顶部,“在眼睛里读心”。 她似乎同样擅长用声音解读情感。 这些技能可能有助于使她免于遭受极少数社会灾难。 然而,这些技能可能直到她二十多岁时才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为什么黛娜逃脱了诊断,以及为什么她应该这样做。 本章的下一节将总结她属于有时被称为“更广泛的自闭症表型”的证据。 在那之后,我们将看看为什么尽管如此,她从未吸引过任何正式的功能失调的标签。
相当奇怪
在15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家人在沙滩上,他们正在与另一个年轻的家庭交往。 父母们互相交谈,孩子们在玩耍。 突然,他们意识到黛娜不见了。 她没有和同龄人一起玩,而是爬上陡峭的岩石。 她回过头来,再次回到岩石上。 攀岩的爱好经常引导她走上门口,墙壁,悬崖,树木,甚至屋顶,直到她二十出头。


虽然她通常很随和,性格善良,但她偶尔会很快爆发出极度的愤怒、痛苦或恐慌。 让她感到怪诞的事情是恐慌的主要来源。 她记得对泰迪熊失去的眼睛感到恐慌,对狂欢节人物的惊恐,对带有巨大纸质马赫头的人物的惊恐,当她的母亲告诉她她有蛇臀部时感到恐惧。 娃娃们惊恐万分,用它们扭曲的粉红色的头和四肢以及翻滚的眼睛击退了她。 多年来,她最喜欢的物品是一条皮毛,她称之为蛇的锡利。

大概是愤怒,或者某种对自由的迫切需求,这使得她在小学时在操场上与男孩们在操场上如此激烈地战斗。 花了四个男孩才抓住她并留住她,因为她挣扎得很厉害。 除了千斤顶和溜溜球,这是她唯一“加入”的游乐场游戏。 她记得看着其他孩子用拳头拍《一个土豆两个土豆三个土豆四个》,感觉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意义,但在那个年纪却没有发现这一切的倾向。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通过Opie收集的游乐场圣歌等[ref]来阅读,这些圣歌曾经对她来说意义不大,而她小时候也很少被吸引。
她自己没有发起假装游戏。 她记得在一个五六岁孩子的聚会上,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一个假装的断头台,孩子们抱着胳膊做一个拱门,同时激烈地高呼头颅被砍掉:小黛娜没有办法这样做,无论多么坚定。 她拥有的玩具骑士因其美丽而拥有,她喜欢根据它们的颜色排列它们,并欣赏它们华丽的闪亮:它们从未用于模拟战斗。 她喜欢在浴缸里玩泡泡。 她喜欢穿过她母亲的抽屉,里面有硬币和别针。 她喜欢旋转硬币,但可能一次不会超过几分钟 – 经常试图一次尽可能多地旋转。 她喜欢撇石头,在有或没有陪伴的情况下,她可能会做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 爬树既有内在的乐趣,又有隐藏她的理想结果。
她学会了很多耐心的游戏,一些在十几岁时极具挑战性的游戏,还发明了各种纸牌游戏来与想象中的对手一起玩。 她怀疑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避免她可能输掉比赛的竞争情况。 在十岁左右,她刚刚遇到的人告诉她,“你害怕失败而死”;她当时大吃一惊,但已经意识到这句话的近乎真实和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她认为,恐惧源于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可怕徒劳。 一个总是让她困惑的表情是“可以更努力”:她怎么能?要么她全力以赴地尝试,要么她根本没有尝试。 后来她变得勇敢了一点,学会了几个中等难度的纸牌游戏,她很高兴地与其他人玩。 建造纸牌屋也是一项特别喜欢的活动:黛娜非常擅长这种平衡行为。
大约九点钟,黛娜发现她喜欢其他孩子认为是折磨的东西,即“中国烧伤”:紧紧握住手腕,双手向相反的方向旋转,拉扯皮肤。 她在操场上走来走去,邀请人们通过给她烧伤中国烧伤来与她互动。 直到今天,她仍然觉得轻微的触感非常不舒服,如果不期待的话,她很可能会猛烈地惊吓一下——这已经引发了一些不恰当的人生意义归属。 她在电视上看网球时曾两次受伤,一次是脚被割伤,一次是手指骨折,直到比赛结束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
小时候,黛娜在触摸方面有明显的感官问题。 她需要被牢牢地塞进去,上面盖着一块厚重的鸭绒,否则她会感到飘的,不安全的。 她不会容忍衣服紧紧地搂在脖子上,而是坚持把事情紧紧地放在腰上,否则她会感到松弛;而且没什么刺痛的! 她仍然倾向于从服装上剪掉标签,因为它们惹恼了她。 她讨厌穿鞋,只要有可能就赤脚去(包括十八岁时赤脚进入伦敦西区,为什么不呢?)。

到了晚上,她的血液在她耳朵里涌动和撞击的声音和感觉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她有一个响亮的滴答作响的时钟来淹没它,她通过将歌曲的话语融入蜱虫中直到她入睡来处理这种侵入性的声音。 选择她的衣服要么是因为它们舒适,便宜,易于照顾和视觉上可以接受,要么是因为她发现它们天生美丽 – 它们不是因为她在里面的样子而被选中。 她尝试过一次剃掉腋窝(哎呀!),可能已经试了两次口红(又是哎呀!)。 她成年后只去过理发店两三次,她的母亲小时候剪过头发。 相反,她通过感觉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主要是“瞎子”。 结果通常不会让她陷入困境。
无花果,木薯,桃皮等各种食物的触觉品质会引起干呕。 气味对黛娜也很重要。 因为她每次在蹒跚学步时都会呕吐,因为她每次给她的鳕鱼肝油添加维生素时都会呕吐,所以她在三岁时患上了佝偻病前的疾病(及时捕获)。 在处理猫粮时,她仍然经常叽食,或者更糟糕的是狗粮,气味和质地都对她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小学时,铅笔、纸和小浴缸里的白胶糊都是最受欢迎的零食。她还发现,年轻的酸橙叶,紫红色和金银花中的花蜜,以及野蒜花的茎很美味。 在中学时,她或多或少地停止吃文具,而是继续不羁地采摘和吃野外小吃。
黛娜曾经用手指看世界,她的母亲和她讨论过这项活动,认为这是对事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 她会猛烈地挤压,按压和工作她的眼球,喜欢这种感觉和创造的图案;她仍然这样做。 她吸吮着嘴巴的顶部。 她的每个食指根部周围都有永久性的褶皱,这是因为她一生都在用力地弯曲它们,远离她的手,享受指关节的强烈感觉。 她的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内侧也有坚硬的皮肤,因为她习惯于用力摩擦它的隔壁手指。 她喜欢先向右捶住脖子,然后向左捶住脖子,感受头部与身体的联系。 其中大多数很容易隐藏:世界不需要知道它们。 她喜欢在手上制作唾液泡泡,但很早就知道这引起了其他人的厌恶,所以把这个习惯保密了。
尽管有一些小的奇怪之处,但黛娜在学校和家里的大多数行为在社会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她对自己公司的喜悦,以及她倾向于长篇大论和提出困难的问题,被视为哲学倾向的证据。 她很早就读到了快乐,没有被视为功能失调,她对生日和电话号码的记忆被视为理想的资产,她出色的拼写为她赢得了学校的拼写蜜蜂。 只有兄弟姐妹的关系给了她任何早期的训练,让她在期待事情有时会出错。 当中学开始出现问题时,黛娜逐渐停止了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努力,仍然把一些精力集中在艺术上(在这所学校,每个人都可以在艺术上取得成功),并付出很多努力来避免麻烦,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被确定为“一个问题”将被视为最糟糕的麻烦,完全失败。 经过多年不断尝试“做对”并取得成功,突然之间,在中学这样做不再轻松。 这可能压垮了她。 相反,黛娜一直善于隐藏不被认可的特质,现在她为自己相当有限的社交技能增加了回避挑战和镜像。

努力做到正确
她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写了这首诗:
剪一朵花,它不会流血
汁液从你的刀刃中抽出
– 你的爱 –
我的自我转动吗我给自己建了一个玻璃
屋 你看,想着你看见我
你看你自己
你微笑着,喃喃自语爱
,称之为联合
,我会称之为
最冷的分离。
当她的情绪的热度照耀出来时,她试图通过镜像以这种方式隐藏起来的尝试被颠覆了,有时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极端强烈的情绪不安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家里发生,直到中学的一半。 在这些阶段,黛娜变得完全口齿不清(这仍然如此),有时长达一个小时,在此期间,她不希望人与人接触,直到她的平衡完成了一些自我恢复。 当她发脾气时,她会经历非常短暂非常剧烈的冲动,这些冲动通常会迅速溶解在上述眼泪中。 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她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弄清楚在引发它的情况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黛娜来说,在这种时候把自己从别人身上移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她无法解释任何事情,然后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解释,并且往往会产生可能使她进一步陷入难以言喻的痛苦无助和愤怒的反应。
十八岁时,黛娜的班主任已经认识她七年了,她很不高兴,因为她忘了提前请假一段时间。 第二天,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告诉她,她“告诉全班同学,黛娜的麻烦在于,她的世界只是黛娜和其他人”。 黛娜当时对此的反应是典型的崩溃,不可阻挡的眼泪泛滥,并迅速逃离其他人的存在。 但回想起来,她明白了老师的观点。 以下是黛娜所认为的意思的几个例子。
- 没有意识到人们认同他们阅读的书籍中的人物;她在二十多岁时从一个当黛娜说她从未这样做过时表示惊讶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一点。
- 假设她相当坚定地关心为当前的共同利益做出建设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对她的朋友来说,而她不必用口头暗示和一般的“phatic communion”来维持它(这与AS伴侣认为说“我爱你”一次应该足够的故事相似) – 纠正这一点需要她保持警惕, 它不会毫不费力地发生。
- 陈述她的观点而不记得以某种方式提醒听众,这些观点只是她的观点,她确实相信其他人对他们的观点有平等的权利(这些命题对她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 没有意识到一个人表达的需求可能会使另一个人感到有义务进一步推动这些需求,无论他们个人是否愿意这样做,并且没有任何权威关系 – 记住和允许这需要她保持警惕,它不会毫不费力地发生。
- 黛娜没有意识到典型的人“战略性地表现出情绪来影响他人的行为”(Rieffe et al 2000,p.195) – 黛娜直到最近才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东西,而不是常态。 即使她明白自己注定要发展这种能力,但她的感受往往爆发得比她无法控制它们的速度更快——这一直是她遇到或创造的许多社会困难的关键根源。
黛娜(她仍然倾向于)对每个人漠不关心地应用了一个粗糙的万能的“其他”建模。 这包括假设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例如,她对待老师与其他人一样 – 而不是优越 。 以下是阿斯伯格(1944/1992)对他的案例研究的看法:
“他们只遵循自己的愿望兴趣和自发的冲动,而不考虑外界施加的限制或处方。 他们理所当然地平等对待每个人,并以自然的自信说话。 在他们的不顺服中,他们缺乏尊重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没有表现出刻意的脸颊行为,但在对他人的理解上有真正的缺陷。“(第81页)
她在这段经文中强烈地认识到了自己。 如果规则让她觉得是武断的,除非她有合同义务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她往往会忽略它们。 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大概多亏了有了孩子,黛娜开始直接收看别人的情绪,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在此之前,她的感情只是通过理性受到别人的影响,她的同情是万能的、普遍主义的,如上所述。 现在“打开开关”已经被抛出,不幸的是,她的同理心同样普遍,因此她无法应对例如观看大多数电视新闻所带来的人们的痛苦。
黛娜出生在20世纪心理学的统计方法建立发展时间表之前,产生了“正常”是可取的荒谬想法,并病态化了非典型性。 在她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灾难使她成为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的责任。 她一直很灵活地接受变化和惊喜——只是没有“做对”是没有好处的。 虽然她小时候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当今儿童的典型,他们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症,但大多数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正如Hutt等人在60年代初观察到的那样[ref],诊断标准证实,自闭症的奇怪行为在数量上是奇怪的,而不是质量上的。 她可能做了比孩子们做的其他事情少,但她没有强迫性地做任何事情。 她没有继续做引起不利关注的奇怪事情:她停止了跳跃,而是保持微笑。 那么黛娜“真的是个常客”吗?还是她只是擅长远离麻烦? – 或者这些是一回事吗?
黛娜一再发现,她的单向性情可以变成好账。 如果她知道任务是什么,并且她相信任务是她的,那么她就会带着遗嘱出发! 如果她看到原因,她有能力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多。 尽管我们已经描绘了一幅她认为完全正确的恐惧驱动回避的图景,但通常如此成功地让她远离暴力可怕的感觉,以至于她很少经历这些感觉。 因此,在实践中,她的生活一般方法是一种有弹性的信心和起床和走动。 但由此可见,使她远离诊断的因素之一是隐瞒,这与本章中包含的披露和本书其他地方讨论的相反。 镜像技术显然让她在用它来管理社交生活时有些不安。 但它有重要的优点:它保持了与他人沟通的开放渠道;这是了解人们及其感受的好方法;它保持了她的可接受性。 最终,镜子融化了,其他人直接进入她的头脑和心灵,呆在那里 – 正如他们注定要的那样。
那么,我是说“我是阿斯皮”吗?甚至“我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 – 或者不是? 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区分,答案不可能是“是”和“否”,但它是。 托尼·阿特伍德(Tony Attwood)说:“人们认识到,这种情况处于无缝连续体上,溶解在正常范围的极端。 不可避免地,有些孩子将处于“灰色地带”“9p.145,1993[?]。 我处于那个灰色地带。 正如汤姆·伯尼(Tom Berney)在他的学术章节中所说的那样,诊断是试图对多维现实进行绝对区分。 因此,每个维度都提供了可以划定边界的不同点,诊断标准的性质是,每个分界线的一侧具有“可接受”或“正常”,另一侧具有“不可接受”或“异常”。 在本书的引言中,迈克·莱瑟(Mike Lesser)和我提出了对这些维度的分析:我在这里将把这种分析应用到我自己身上。
兴趣深度
随着你所有意识的狭隘关注而陡峭地注视着,这可能是了解那些从而抓住你兴趣的对象的好方法。 据我所知,我很少全心全意地关注这一点。 当然,我总是能够根据需要转移注意力,尽管有时会感到不适。 被陡峭的注意力隧道化意味着其他人可能会与你擦肩而过,如果其他人确实受到冲击,它可能会以一种响亮,坚持和潜在的令人震惊的方式发生。 我自己的童年并没有被那些徒劳地试图引起我注意的人所困扰:我认为人们很有趣,我并没有因为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而失去动力。 因此,尽管我紧紧地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可能比大多数人要大,但它既不会让我表现得令人无法接受,也不会让我有任何非常不寻常的能力。
关注的广度
有时,我可以放慢自己的速度,以专注于细节,注意到光线通过露珠折射,注意到通过一段音乐播放的即兴表演,注意到草叶中的小真菌。 像这样的小快乐本质上是和立即令人满意的,但对我来说是罕见的和短暂的。 那些兴趣总是注重细节的人往往会错过更大的图景,他们往往会以其他人认为令人费解和不可接受的方式行事。 主宰我生活的两个主要兴趣——首先是语言,然后是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巨大的范围。 这些广泛的利益并没有激起其他人认为令人费解或不可接受的行为。
操作阈值
作用水平阈值影响从一个焦点兴趣到另一个焦点兴趣的循环速率。 当不受个人兴趣话题的驱使时,我倾向于迅速前进。 即使我个人参与其中,我也倾向于在主要兴趣和其他一些要求较低的兴趣之间来回切换。 当不那么投入但需要留在任务上时,我以各种不显眼的方式自我稳定,这些方式可能被认为是“隐藏的刺激” – 例如试图将视野划分为许多矩形部分,这是五的倍数。 虽然在课堂上非常不专心,但伪装得非常好,以至于拥有我母亲所说的“蚱蜢头脑” – 并且现在可能被贴上多动症标签 – 从来没有让我陷入困境。 它有助于我建立很多联系,并且不会错过太多正在发生的事情。
唤醒速度
痛苦的唤起是如此迅速和失控,以至于它震惊了其他人,使社会表现力丧失,迫使我暴露了我不可接受的面孔。 避免这种情况的愿望激发了镜像技术并减少社交接触。 在崩溃的特定情况下,恢复镇定是唯一有效的策略,否则情况就会恶化。
总体可用关注量
在醒着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似乎很少成问题。 在熔毁时,加工能力不堪重负,可用注意力枯竭。 更普遍地,失去信心涉及退回到任何看似安全的事情上,从而减少分散的注意力。 大多数时候,高度的信心得到保持,并伴随着他们充足的注意力,包括局外注意力。
在局灶性兴趣之外维持功能性觉醒的能力
在崩溃的时候,它不再是自动的,主观上毫不费力地意识到我关注之外发生的事情,包括监控和适应其他人的行为和反应。 注意力的稀缺也会降低这种能力,并且可能是由于极端的处理需求或由于抑郁或丧失信心而导致的意志丧失。
利益得到社会认可的程度
我成长的环境欢迎并尊重我的智力转向和平等主义,并接受我所揭示的这些奇怪之处:这无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灾难并增强了信心。 我对语言及其与思维的关系的特殊兴趣促使我获得了三个大学学位。 平等主义正好符合家庭传统,并转化为政治行动主义,多年来,这给我找到了许多同志。 即使我对各种真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兴趣是否在开发早期就包含了语言
这是在一个人的成长岁月中被社会接受的关键,因为在一定年龄之前学习说话往往被视为适当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很早就学会了说话,似乎已经迅速获得了大量的词汇量,自信而称职地部署了。 直到大约三十岁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思维不仅仅是我逻辑上斩断的引人注目的词语:直到那时,我完全错过了视觉思维的潜力,而且它仍然在我身上发展得很差。
情感质量
愤怒和痛苦是致残的。 除了在崩溃的状态下,我的性情往往是阳光明媚和随和的。 一般来说,我有一个自信和积极的取向,这可能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显着影响,即我只做我期望擅长的事情;几乎从不尝试两次出错的事情;在任何特定场合都有最低限度的具体期望;反复记下那些让我快乐的事情和事件,在每种情况下都寻求这样的快乐。 面对其他人,我经常微笑,人们往往会回以微笑。
沿着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气质或环境的微小差异都可能导致行为的重大转变。 而这种转变反过来又意味着我会收到一种负面信息,这种负面信息往往会引发我彻底的社会关闭。 在宣布我作为自闭症表亲的身份时,我承认不仅与拉尔夫史密斯所谓的“闪亮的Aspies”有亲戚关系,而且与那些被认为“功能低下”的人也有亲戚关系。
作为一个孩子,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特殊帮助或治疗的问题。 我讨厌引起别人的注意,除非我完全确定如何在不“崩溃”的情况下继续前进。 被注意到有问题是世界上我想要或期望的最后一件事 – 我很少经历或体验到这一点。 我宁愿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自己的项目。 我的主要,通常是成功的,至少十年的项目没有遇到麻烦。 我会经历被视为一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仍然被赋予一个功能障碍的标签,认为它是灾难性的。 人们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才开始担心我,谢天谢地,只是轻轻地担心。 当然,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帮助,无论我多么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但这些差距从未引发过那种危机,这意味着我被视为一个问题。
我没有任何意识,因为我长大后与那些比我更“相同”的人相比,我个人截然不同。 我知道能够拼写一切并能够记住整首诗,生日,电话号码是不寻常的。 其他人在不同的事情上做得异常好。 在我成长的社会环境中,作为黛娜的“不同”的人,从来不意味着被排除在外,从来不意味着被当作外星人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让孩子“难以区分”的目标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说是可取的。 后来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与我周围人的潜在疏远差异。 突然之间,我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我必须弄清楚如何保持不显眼并继续被包括在内;我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来避免麻烦。

随着我的成长,我意识到的任何差异都有助于我的信心,而不是破坏它。 我知道我是知识精英中一个杰出家庭的典型成员,他们可能心里很古怪。 我知道最怪异的人可能有最好的想法。 我在一个有着相似态度和价值观的人的社会中长大,在我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拒绝。 我的行为被视为典型的原始哲学家,而不是越轨行为。 即使在这个狭窄的领域之外,我感兴趣的领域也受到社会的重视。
我怀疑大多数“自闭症表亲”以及那些在光谱上更清楚的人,都会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即作为一个有趣和不寻常的家庭的成员长大。 运气和关怀可以给他们一种很好的方式变得特别的感觉,也有一种归属感。 在我看来,重视我的兴趣并感到我的归属感似乎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有益特征,可以复制。 如果人们的兴趣和能力包括那些在家庭之外赢得社会尊重的人,那么他们的信心和动力可能会得到补充,而不是被社会期望的遭遇所消耗。 有了这些资产,他们可能有足够的反弹来承受更多的生活打击而不会发生灾难。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两个世界之间移动,新约世界和非新界世界。 从我所处的位置来看,在人类流动的浪潮中,没有明显的边缘。 我通常对我明显NT的朋友感到快乐和舒适,就像我对我明显患有自闭症的朋友一样。 也就是说,自闭症关系中常见的缺乏社会需求对我来说是非常放松和愉快的。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我感到与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超然,但这并不能让我感到悲伤或不舒服。 有点超然通常是一件好事。 这些情况可能最常涉及典型的人做他们认为比我更有社会回报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疲惫,维持一个不断适当的社会形象的努力似乎越来越不值得。 那么,我能不能通过提到我的自闭症表亲身份来原谅我可能越来越缺乏社交优雅呢? 当我意识到有人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安或失望时,我是否应该“披露”这是“因为我有点阿斯皮”? 这就像声称有权使用轮椅一样,因为一个人偶尔会扭伤脚踝。 我不值得任何特别的考虑。 然而,在自闭症研究的世界里,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从业者承认他们和我一样远离正常,并认识到他们自己与“受试者”的亲属关系,他们倾向于采取如此优越的立场。 在这方面,否认任何优越地位是培养对平等人格的尊重和承认的关键。
正如西蒙娜·威尔(Simone Weil)所说,“我们的社会人格,我们的存在感几乎依赖于此,总是完全暴露在每一种危险之下……任何削弱或破坏我们的社会声望,我们的考虑权的东西,似乎都会损害或废除我们的本质“ p88 从…和压迫?
如果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的社会声望被摧毁了,她的故事可能会多么不同。 她不是精英中无忧无虑的成员,她可能是那些咕噜咕噜或不恰当地问候陌生人的尴尬人之一;她可能已经完全放弃了“试图把它做好”,超越了她狭隘的完美控制范围;她可能是一个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影响力的被抛弃者。
区分正常与异常的边界,无论它在哪里适用,总是由正常性概念的先前历史决定的。 每一次诊断和披露的行为都会将个人推向官方不可接受/不正常的一面。 这成为正常概念的直接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对该边界有潜在的影响。 每一个诊断的例子,其中个体的自闭症特征不那么尖锐地蚀刻,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边界转移到中心:现在更少的人算作正常,尽管他们可能还不知道。 我的形象是正态统计分布的贝尔曲线的大投球手帽子形状。 总而言之,诊断医生正在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切除非典型边缘。 但是,瞧! 当他们这样做时,典型的中心收缩,并出现一个新的轮辋。
这不是我想为之作出贡献的进程。 但边界还有另一种改变方式:它不是向越来越严格界定的规范局促,而可能是一种不同的边缘。 这可能是值集之间的区别。 按照目前的标准,通往社会可接受性的道路是一条伪装、隐瞒和展示的道路:这是一条胡说八道的道路。 它最重视演讲技巧;它贬低了过程中的其他一切。 我们不必同意,这些是可以接受的价值。 我们可能会看到,成为那种吸引自闭症谱系诊断的人可能意味着要有一个体面和谨慎的性格,以及对“做对”的关注,其中包括对真理的关注,并可能赋予巨大的工作能力。
如果人们声称自己无法接受支撑当前规范的交易者的价值观,那么这个过程与授权诊断的过程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的过程,如果足够多的社会上可接受的人做出这种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文化转变可能会发生。 如果你想站起来,自己被算作自闭症表亲,请去 www.autismandcomputing.org.uk (不再活着)登记你的立场。
1 即参加桑德兰大学自闭症研究部门组织的达勒姆会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