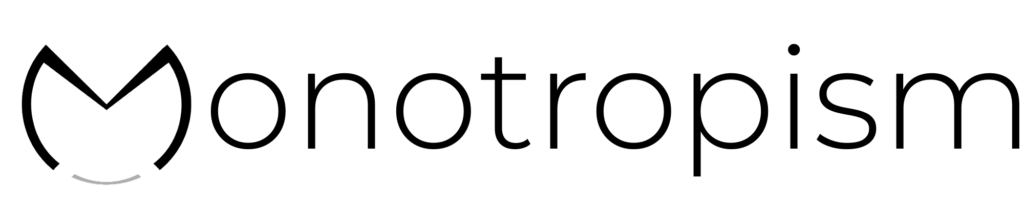作者 :黛娜·KC·默里
1995年,“自闭症的友谊”,自闭症心理学视角,达勒姆会议自闭症心理学视角
本文是 《艺术……一种积极的生命必要性》(2013)的一部分。
背景
大約五年前,我以語言學家的身份來到自閉症,對語言在思維中的作用有了深入的解釋,並且認為我對心靈的普通運作的解釋可能對於理解自閉症的功能障礙有幫助。 从那时起,我一直试图找出我是否正确,部分原因是通过了解一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特别是一个 – Ferenc Virag,现在十六岁 – 相当不错。 我必须在友谊的基础上认识他,正如他的特殊学校的校长伯特·弗兹(Bert Furze)所要求的那样。
当伯特敦促我和他的一个学生交朋友时,这很符合我自己的意图 – 尽管我根本不确定该怎么做。 我不是一个实验心理学家,我希望能够观察一个自闭症患者的自然行为,包括观察他们与我的无干预存在的关系。 以自己的方式,它一直是一个实验。 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一个我在费伦茨有共同兴趣的人。 我们都喜欢自然,光线,折射和反射,在其中找到美丽。 我们都喜欢控制物质:制造东西,融化东西,让火花飞起来;我们都喜欢计算机图形学的潜力。 当他感到沮丧时,费伦茨有时会严重伤害自己,咬住他的拇指直到流血,喘他的额头,等等。 他锉牙,吃昆虫,用舌头测试电池。 他是一个选择性的双语哑巴,最近被评估为理解多达四个单词的话语。 虽然他不会说话,但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马卡顿标志,其中只有一些我理解。
这篇论文的大部分篇幅都致力于讲述我与他关系的轶事。 我没有试图掩饰他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位艺术家 – 一位动画大师 – 并且因为他已经同意出版下面的轶事。

自闭症和非自闭症思维:推测
在我看来,关于自闭症和非自闭症思维之间差异的一个有用角度是,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许多紧密相连的共同活动兴趣(见图1),但自闭症患者很难一次维持多个。 普通的头脑可以很容易地应对环境,甚至是充满活跃和互动的人的环境。 自闭症患者的注意力是彻底的 – 隧道或单向的(见图2)。 其注意力隧道内的事件可能会导致过载,其注意力隧道外的事件往往不会集成。 孤立的兴趣区域不能为正常的消化样传播认知效应的过程提供足够的兴趣间联系。
因此,如果某些东西将注意力从这些深层注意力隧道中转移开,其效果将是突然的,并且可能会引起极端或震惊的反应。 在普通的社会交往中,我们不断地用言语来吸引注意力,侵入对方的思想。 对于刚性单性1,即。自闭症患者,处于这种言语接收端的人,它将作为具有挑战性的行为发挥作用,既寻求关注又极难处理。 (“共享注意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需要比这里更详细地研究。
与典型的婴儿不同,自闭症患者无法轻易发展出那些丰富相连的兴趣体系,这些兴趣体系在面对多样性时具有弹性。 变化往往会让他们感到困惑和惊慌。 虽然我们迅速建立网络的模糊网络,但一个单向性个体将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利益之间的任何相互联系 –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兴趣内部联系可能会变得无限复杂。 他们所有的利益都将是高度模块化或封闭的lv-特别是,拥有一个孤立的词典或单词库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整合力量:词关系通常跨越整个利益范围,并对其施加一定程度的不变结构。
因此,自闭症对连贯性的追求与任何一种一样强烈,但仅限于局部而不是中心操作领域”。 一些单向性个体可能能够接受范围广泛且涉及大量详细信息的主题,只要该主题上有足够强的边界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比一个典型的人更能掌握整个事情。
关系
此外,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是费伦茨的常客,分享他的兴趣,尽可能地教唆他们,以一种鼓舞人心的方式评论他的行为,并密切关注他们。 很明显,他喜欢这一切 –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变得更加适应我的担忧,更有兴趣与我沟通。 我相信我们关系的一个特殊特征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我一直对他表现得很友好。 共性与一个人有关,让他们的兴趣在言语和行为上指导你的利益。
轶 事
9/92:这是我们每周五的常规下午之一。 费伦茨被要求在空闲时间和我在一起之前完成一个项目。 这一切都完成了,但写了他的名字,他真的不想这样做。 他看着我,看了我一会儿眼睛,然后把纸和铅笔推过桌子给我。 我说,“对不起,费伦茨,但我认为如果我为你做这件事,我可能会和乔惹上麻烦”(这是真的)。 他立即把纸拿回来,继续写下他的名字。 从那以后,我有过几次
“我用”刚性单向性“来形容自闭症,因为一种柔软的、缓慢的但移动的单性似乎表征了唐氏综合症——这个想法是由玛丽安·西格曼(Marian Sigman)的评论引发的,并由我自己的观察证实。 它与模型和人中通常非常不同的一组行为相关。不得不向他解释,如果我顺从他的意愿,我会遇到某种麻烦:他几乎总是合作,事不宜迟。
92/937 在费伦茨的学校礼堂里有一张照片,在切尔西花展上因在当地社区花园的工作而获奖。 他带我去大厅给我看。
5/93 我和费伦茨的班级一起郊游。 教学人员等待,迟到了。 孩子们无事可做,所以一个帮手组织他们做一些他们大多数人非常喜欢的事情,即用从板条箱里选择的奇怪乐器制作一些音乐。 像往常一样,费伦茨以一种希望不被注意到的姿势站在后面,他的头稍微低下,他的四肢蜷缩着。 帮手把他围起来,他愤怒地咬着拇指,然后按照别人的吩咐走了过去,坐了下来。 他看着我,凝视着他,我想是一种强烈的同伴感觉,因为这就是我的感觉,他微笑着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微笑。 我回以微笑,而他又把我的目光看了一会儿。 帮手催促他拿起一个乐器,他毫不费力地捡起一个三角形,然后再次催促,给了它一个打击并停止了。 我对他说,“也许你可以享受自己?”然后又带着一丝微笑,他开始玩了。 94年初,费伦茨使用的是烙铁。 他正在等待一滴焊料从尖端掉落,但他水平握着铁。 我说:“如果你减少表面积…“在我完成这句话之前,费伦茨已经将铁倾斜到垂直方向。
94 费伦茨被证明对计算机动画有真正的天赋;我们决定通过将他创建的每个屏幕(包括光标的每个移动)直接转储到录像带上来记录他的作品。 第一次,我们成功地制作了两份副本,一份给他,一份给我们。 他和迈克之间的沟通 – 我的同事对这个项目的贡献一直是核心“ – 从一开始就很好,因为迈克只关心帮助他理解和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技术没有完全排序:只有一个录音(这次我们打算制作三个 – 就像我们接下来成功做的那样)。 我说,“哦,费伦茨,如果我把这个带回家,在星期一早上把它还给你,会不会好吗?” (明天的第二天)。 他用力摇了摇头。 我感到非常烦恼,我咬紧牙关离开了房间。 与此同时,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那样,迈克走到费伦茨面前,费伦茨拿着那盒成功的磁带,用眼球看着他,“费伦茨,你知道黛娜也真的非常想要它……". 下一刻,费伦茨在厨房里找到了我,紧紧抓住磁带给他,他向我靠过来,并做了一个明显的努力,试图将磁带延伸到我的方向。 我说,“哦,好吧,如果我把它带回家……?" 他一如既往地用力摇头。 我耸了耸肩,告诉他没关系——听天由命,再也见不到它了。
下一次,我们成功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图尔特·鲍威尔的帮助)直接从电脑上设置了一对录音,再加上一台拍摄费伦茨本人的外部摄像机,以及我们与他的互动。 在会议结束时,当我把他的录音带给他时,他拒绝了,表明这是我的。 我非常感动,就像我早些时候一样,他穿过桌子向我推来,最后四个费列罗罗奇(在那之前我只有一个)。
7/94 我们一起坐着我的车,走了四十英里。 就在我们离开伦敦时,交通堵塞形成了,他咬着拇指,S磨我的牙齿和哄咬。 更糟糕的是:在下一个路口,胶带被拉过马路,每个人都被左送去或右走,没有指导,也没有解释。 再一次,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咒骂。 我解释说,当我们和其他一半丢失的汽车一起爬行时,我们只需要在下一个转弯时走正确的路,我给他看了地图和我们不得不离开的道路,我们的目的地在上面清晰可见。 从那时起(没有阅读地图),直到我们重新上路,费伦茨对方向完全有信心,即使我犹豫不决,也急切地推着我,指出即将到来的路口。 随着他的一点点拇指咬合和我一点点咬牙切齿,我们俩都设法保持冷静,并最终到达那里。
7/94 我们一起走过一片长长的草坪。一只猫走出来加入我们,我抚摸了一会儿,费伦茨伸手下去,短暂地摸了摸它的尾巴;我们在猫的陪伴下走着。 异常!打破沉默,用我经常有的一个想法,“费伦茨,”我说,“我经常认为普通人,像我这样的人,更像狗,而像你这样的人,自闭症患者,更像猫”,然后我转向他,问他是否知道我的意思。 他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他向我暗示,也许他觉得自己理解了猫的类比(他们养了一只猫),但不确定其他人和狗。
8/94 费伦茨和!我的狗加入了一群漫步者,沿着哈德良长城露营。 没有椅子,三十六小时他不会坐下。 最终,在许多人的劝说下,他故意去拿那个大木箱,这是营地里最豪华的座位。 他在火堆旁找到一个空间,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坐下来。 在前几天晚上,他对火的迷恋 – 特别是他想要融化其中的塑料,并使火花飞舞 – 引起了一些紧张。 露丝巧妙地扭动着说,如果他被允许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做这件事,他会开心几个小时,一直打出发光的品牌,这样他们就会把火花射到黑暗中。 今晚,他正试图与塑料融化妥协,并在将小碎片放入火中之前将小碎片包裹在铝箔中。 不幸的是,即使如此小心,它们在融化时也会闻到气味,费伦茨发现自己被大喊大叫了。 在猛烈地侧身掐着头(好像他可以像耳朵里的水一样把酒抖出来)之后,他把一根手指刺在鼻子上,产生了一股可怕的瞬间鲜血。 针对他的诽谤情绪立刻变成了同情的关心。
他和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无缘无故地找到了一个容器。 当它装满时,我们匆匆忙忙地回来,当我们靠近时,他拉到前面,几乎打破了一个运行,并且(再次没有提示)他把它们交给其他人。
两个晚上,他几乎不躺下,没有睡觉。 他不会进入为他搭建的帐篷,他不会躺在他同意与另外两个人分享的帐篷里。 第三天晚上,我们让他帮忙在我附近搭建一个帐篷,把他的睡袋放在里面。 凌晨一点左右。雨开始下,每个人都走向他们的帐篷。 费伦茨站在他和我之间,一动不动。 我恳求他弯下腰,进去,我向他展示那里很好,我指出,如果雨越来越大,我敦促他弯曲膝盖,让我脱掉他的鞋子,想想他有多累。 他很坚定。 我说,“费伦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在你躺下之前,我不能躺下。 他脱下鞋子,躺下。 我们位于一个英国遗产罗马遗址。 在他捡起的一些细碎石和一块狭窄的木板上,费伦茨非常小心地刻上一个图案,经常站回去看效果,然后到处摸它。 我钦佩他的所作所为,并这样说。 后来,回到营地,他和我走下来,看看远处山丘和云层的日落景色。 他急切地拍了拍我,对这美妙的景象做了一个扫地指着的手势。我说,“是的,这太神奇了 – 光和阴影。 然后我又补充道,“嘿,费伦茨,你知道你刚才在砾石里拍的那张照片吗?”他同意了,“我以为那都是关于光影的?”他给了我一个最决定性的点头。
10/ 94 由於我們無法控制的事件,這是我們在一起幾個星期的第一個星期五。 我通常在1点15分后不久到达学校,今天在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学校大门之前,已经快过了一半。 希拉和博耶娜都让我知道我是多么不耐烦地等待着我。 他们向费伦茨指出,如果他想确保我来了,如果他愿意使用语音,他可以打电话给我家并检查。 显然,他已经认真考虑了这种可能性。 当我了解了这一切时,我已经在离开者的房间,他站起来,脸上满脸笑容,然后走出门,我跟着他,去了技术室。 在那里,他一心一意地忽略了一切,除了自上学期以来他一直在我公司试验的(非常安全,精心设计的)电气设备。
我们一起发现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制造一个发光的“元素”,在不绊倒安全机制和切断电流的情况下保持令人满意的热量。 已经相当系统地探索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导线以及电压的变化。 我们俩都喜欢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当电流碰撞时,火花会飞起来。 一周,当我们探索这些属性时,费伦茨点亮了一整串小灯泡,其中的电路部分由音乐布景中的三角形制成。 一个星期,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一块木头上画闷热的线条。 我向他指出,他所做的是使用与使烙铁热相同的技术。 他看着我对面,说:“这真是太有趣了! 现在我明白了!表达。
12/94 这是学院!假期 – 圣诞节前三天 – 我已经向费伦茨保证,我们终于会回到卡德菲尔德。 当我(从他的休息中心)接他时,他用C标志迎接我 – 非常紧急 – “是的!我们要去卡德菲尔德,“我说,一种满足的表情传遍了他的脸上。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俩立刻被建在大池塘上的新木制走道所震撼。 费伦茨想马上继续,但当我说我们最好向居民问好并检查一下是否没问题时,我没有异议。 在快速访问了餐厅之后 – 费伦茨对新桌布(可能是十年或十五年来的第一批新桌布)有点激动 – 我们回到了冰冻的池塘。
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尽可能地打破最大的冰块。 费伦茨很快就为此开发了一种出色的技术:他找到一根长棍子,用它把他能伸到的冰上,很快一条裂缝就出现了,我把最新的一块从水里弄出来。 每一个都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小块 – 小心翼翼地刮擦,勤奋的黑客攻击,投掷,最终(尽管仍然不完全)将它们放在头顶上。 他拍了几片冰盖,邀请我去听它们的声音,把它们举到太阳面前,看着透过它们的光,沿着剩下的冰块反弹小碎片,最后把每一块有价值的碎片都旋转到空中,它们几乎漂浮在旋转的地方。 在那之后,在我的要求下,他把我带到了田里的地方,几个月前,他整齐地踩出了一根玉米线(见照片)。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排队时太阳在哪里,他已经果断地点了点头。 正如我试探性地猜测的那样,这条线指向太阳曾经去过的地方,“所以,你让这条线指向太阳?” – 另一个决定性的是。 当我看着他的线条的照片时,后来我意识到它与直线度的轻微偏差是太阳在天空中的小运动的函数,而他小心翼翼地把它踩了出来。
94年代末,费伦茨和我去南肯辛顿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看玻璃。 在拱门,费伦茨把我带到平台上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向下看隧道,弯曲到黑暗中。 他朝它打手势,确保我分享他的注意力,我专注于同一个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凝视了一会儿,然后走回平台。 现在,他急切地指着线间,来到啮齿动物忙着四处乱窜的地方,擦掉所有可食用的垃圾,“哦,是的,”我说,然后补充道,“它们小心翼翼地不碰电轨”。 在博物馆,我们对玻璃展示有点失望:它太杂乱了,没有什么机会被正确看待。 费伦茨显然觉得太多了,我们俩很快就修好了楼下的餐厅。 在那里,他以一种完全有序的方式排队,只是在闻到糕点时破坏了正常的外观。 我给他拿了一个糕点,加上奶油和一杯碳酸饮料;我有一壶茶。 当我准备好喝第一口茶时,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擦光了,并要求更多。 我看着我的钱说,“如果我给你钱,你会去拿吗?”他坚定地摇晃着他的霕虹灯。 所以1说,“好吧,那恐怕你不得不不行,因为我想坐在这里喝我的茶。 他站起来,拿了足够的钱买了另一个糕点,然后走到柜台拿起一个 – 实际上,拿起两个,这导致我短暂地干预。 然后他把它带到收银台,给收银员看,把钱交出来,等待零钱,然后带着糕点回到桌子上。 他以前只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在巨大的压力下,每一步都在唠叨,我告诉他,“干得好,”补充道,“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知道,费伦茨?”但没有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穿过马路前往科学博物馆,那里还有一个专门用于玻璃和玻璃制造的画廊。 我们发现它比它的艺术邻居更令人满意。 在费伦茨的坚持下,我们观看了1979年铸造厂玻璃制造过程的粗糙循环视频。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正在等待行人灯在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亮起。 一个陌生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注意到绿人终于点亮了。 但费伦茨做到了,并焦虑地推了我一下。 过马路时,他一般的外表总是封闭的,对周围的场景一无所知。 在此之后,当我们一起外出时,我有时会向他指出,如果他愿意应付过马路,他可以自由得多。
1994年圣诞节,我把费伦茨带到我家,向他展示我们装饰精美,非常高大的树。 他瞪了一眼,然后避开了眼睛,“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问:“是的!”他果断地点了点头。
95年1月下旬,我找到了当地的玻璃厂,他们愿意让我们在一个星期四下午参观。 当我们接近它时,我告诉他,他很可能实际上无法做任何事情,尽管他有可能这样做。 他似乎接受了这一点。
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炉子,窑炉和奇怪的工具。 费伦茨渴望探索一切;我说,“对不起,我们只需要等到有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触摸到什么”。 他只是让自己从那时起克制,但几分钟确实拖了过去。 最终,我打电话给一些楼梯,一个和蔼可亲的管理员 – 可能是我安排访问的她 – 下来并开始向我们解释事情。 费伦茨专心地听着她所说的一切,看着她所描述的用途的物体。 他发现了一堆精心订购和贴标签的彩色玻璃片,他带她去那些人那里解释。 他也想有一个,但我告诉他,他们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她的。 在另一个房间里,用于玻璃抛光/研磨的轮子正在旋转,而工匠在其中一个上塑造一个塞子,费伦茨专心致志地看着它。 当她停下来时,他抓住了许多等待他们最后修饰的普通玻璃塞中的一个,并被允许将其放在转动的锉刀上。 他用他惯常稳定的手握住它,有目的地,平稳地使它在每端形成一个几乎完美的矩形正方形部分。
传来消息说,下午的玻璃加工已经在铸造厂开始了,费伦茨毫不犹豫地停止了他的申请。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观看了三人小组表演他们微妙的玻璃加热舞蹈,最终将一个巨大的彩色气泡挤入模具中。 Ferenc设法远离人们的视线,同时与他们参与的过程保持密切联系。 当他被告知他不能自己在任何软化的玻璃上工作时,他做得很好。 但是,当有机会对一小块仍然熔化的玻璃做事情时,他表现得像闪电一样,这块玻璃被倾倒了。 他发现了一块碎砖,并及时将其小心地压下,以打动冷却的斑点。
1995年3月初
有一场小雪落下,已经落在伦敦温暖的空气盆地之外。 脱欧班当天要去圣奥尔本,去寻找雪。 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未受破坏的白色。 几乎立刻,费伦茨开始滚雪球,直到它太大而无法滚动。 然后他离开大约二十英尺,开始向第一个球滚动另一个球。 这被打包到位,而我得到更多。 其他人在我们继续建设时去看网站。 显然,不要成为一个雪人;一旦有足够的质量到位,费伦茨就开始形成一个四角结构,侧面平坦,略微倾斜。 !保持积雪的供应,并找到一根我认为可能有用的长直棍。 立即,费伦茨以宽阔的扫掠动作使用棍子将侧面压平。 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扎扎实实地工作,没有休息近一个半小时。 当时间用完时,结构就完成了。 它是一个坚固的堆积雪基座,底部约四乘四英尺,高约三英尺,顶部约三乘三。 我们让其他人看一看;费伦茨短暂地爬上了它(它很容易承受他的重量)。 他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
1995 年 3 月
在学校集会上,我向哈伯勒展示了迈克·莱瑟和我与费伦茨一起制作的电影:我们所有的名字都在扉页上拥有版权。 费伦茨(当我们制作后不久,当我为他演奏它时,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非常强烈地观看了这一切,并在它结束时立即冲向我,使Makaton标志为“更多”。 那几个月,他在AES中没有迹象表明他目前知道自己曾经玩过一段美好的动画时光。 我答应他写信给他的父母,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周末见到他。 所以,五天后,我在哈克尼接他,把他带回我的地方。 我们直接上楼去电脑。 在我儿子的一点帮助下,我们运行了动画程序,我把费伦茨独自留在电脑上,而我则在楼梯上徘徊。 当我进去的时候,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写了一个三十二帧的抽象动画,上面有飞碟和线条相互碰撞。 我恭喜他,确保它得救了,然后继续做家务。 下次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把他的短片和我儿子弗格斯稳步旋转的数学衍生动画结合起来,并在他自己的动画中添加了一些对弗格斯独立生成的序列的明确引用。
结论
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理由为什么其他人不应该在一个人发展的任何阶段建立起来。 我的存在显然牢牢地植根于费伦茨的意识中,所以可能影响我的东西也会影响他。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一贯的共热带,我们无法知道。 但迈克的共热带计算机支持似乎对费伦茨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几乎立竿见影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不是都喜欢让别人来讨论我们的利益吗? 我们踊早会发现,其他人和他们的谈话是多么令人恼火吗?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典型的人是缓慢的学习者。 对我来说,了解费伦茨非常有趣和愉快。 以下是我所学到的知识的摘要:
有计划和有目的的behayiour一遍又一遍地展示。 在我看来,与一个典型的人富有想象力的远见能力相比,它所缺乏的就是纳入来自广泛利益的信息的潜力。 任何看过费伦茨动画的人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中涉及了先见之明。
创造性。探索,创造力只需要一个安全的物质环境,为他们提供成为他行为的突出特征。
理解复杂的程序-
(a)在计算机上:他对动画程序的了解比我好得多;
(b)在世界上:他毫不犹豫地预测了三个玻璃吹制者的举动。 我相信,当有动力这样做时,他可以掌握冗长的序列。
出色的空间和生理掌握可预测的行为 – 例如他敏锐而有效地行使控制这些行为的能力;从他使用电气装置时的精确触摸和分钟刻度到他熟练地建造雪基座,从他迅速熟练地操纵冰到他通过专业动画程序对空间变量的同样熟练的操纵。
渴望共同关注 – 他经常向我指出他感兴趣的内容;正如他对学校里任何被调到他的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如果我的注意力在我们星期五的某个会议上徘徊,他有时会把我的头转回去;他显然很享受与我分享,沿着哈德良的哀嚎的奇妙,灿烂,风吹拂的景色,经常对它做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姿态,以确保我也把它带进去。
自我意识;他狂热地凝视着自己的照片;他照镜子,特别是他的牙齿;他复印了他的鬼脸(见插图);他带我去学校礼堂,给我看一张自己在花展上获奖的照片;他通常欣赏欣赏他的作品的人 – 他向我展示它们,并向他喜欢的工作人员展示它们(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任何其他学生,除非在大会上敦促这样做);在我看来,他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所形成的耸耸肩似乎表明了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对不完美控制的辞职 – 这肯定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对听到上述轶事的明显兴趣,表明他渴望获得有关他自我的信息 – 尽管这些一般结论被证明不会引起他的注意(见下文)。 意识到他人的利益:(a)他一再愿意让对我的兴趣产生不利影响的考虑影响他的行为(b)他记得在几个小时后没有完成费列罗·罗切斯,没有来自我有意识的暗示,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相信我会试图向他施加任何压力(c)他决定把他制作的最新视频的副本给我, 几周后,他让迈克告诉他,我真的很想保留那份唯一的副本(我在这里推断出一个原因,这可能是完全错误的)(d)他介绍的蘑菇供所有人使用,当我们露营时,理解定期的,有时是复杂的,共热带的演讲:!从不和他说话,沟通通常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次,他正在等待一滴水从他水平握着的烙铁上掉下来。 我说:“如果你减少表面积…“在我讲完之前,他已经把它变成了垂直的 – 用务实的能力完成了我的想法(或者这只是偶然的?
当我向费伦茨宣读上面的轶事时,我为此道歉,并解释说我需要他倾听,看看他是否记得我记得的东西。 我还解释说,我需要知道其他人读它是否没问题。 他似乎很想听,并密切地出席了会议(尽管S后来放弃了阅读这些一般观点的尝试:它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力 – 不够具体?或者也许写得太密集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相当接近我的文本,只是偶尔简化,定期点头检查我的记忆检查。 大约在进行到一半时,我问他只是点头,因为这更容易。 他摇了摇头。 当被问及他是否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时,他果断地表示他理解“妥协”。
一如既往地感谢迈克·莱瑟(Mike Lesser)多年来的激励和批判性贡献。 今年,我特别感谢他,因为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推进Ferenc的电脑动画,并设计出录制它的方法。 除此之外,他和罗伯特·塔舍尔(Robert Tasher)也足够好心地绘制了我需要的单向性和多向性兴趣系统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