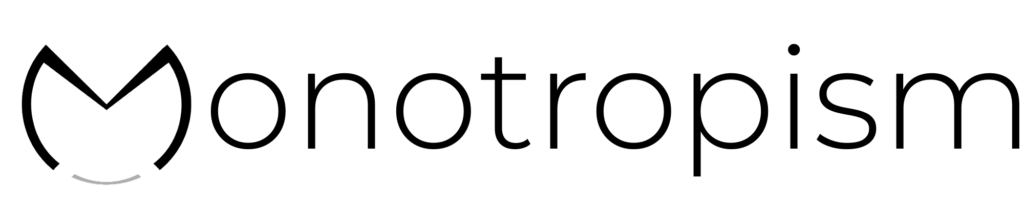作者 :黛娜·默里博士 – 英国
注:这篇演讲后来被扩展为《从 社会角度考虑新 自闭症研究发展中的成人结果》(2007)一章。
来自自闭症2006 AWARES会议:
Dinah Murray博士(www.autismandcomputing.org.uk)是自闭症及其变体领域的工人,研究员,作家,活动家和教师。 她是一位以人为本的规划顾问,居住在伦敦北部,与儿童和(主要是)吸引自闭症谱系诊断的成年人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她作为唯一作者和Mike Lesser以及最近与Wendy Lawson一起发表了大量文章。 黛娜撰写了材料,并担任伯明翰大学远程教育课程和基于互联网的WebAutism课程的导师。Murray,Lesser和Lawson对诊断标准的批评出现在2005年5月的自闭症中。 黛娜编辑了杰西卡·金斯利(Jessica Kingsley)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出柜阿斯伯格综合症:诊断,披露和自信》(Coming Out Asperger: Diagnose, Disclosure and Self-Confidence),并与安·阿斯皮诺(Ann Aspinall)合著了《获得IT》(Getting IT),内容涉及使用信息技术赋予人们解决沟通问题的能力,杰西卡·金斯利(Jessica Kingsley)今年也出版了该书。 她是反应色彩项目的顾问,该项目由NESTA于2005年和2006年资助。 黛娜是 http://www.youtube.com/group/posautive Posautive Youtube小组的所有者。
抽象:
自闭症由一组诊断标准定义,这些标准以文化偏见的方式识别
功能障碍,从而有害地扭曲期望和判断。有人认为,这往往会对自闭症患者的教育和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对其能力的不适当的负面期望。自闭症被更有建设性地视为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人类基本多样性的一个方面。特别关注围绕同理心的问题。讨论了自闭症倾向的许多积极特征的证据。
全文:
自闭症目前仅通过其功能障碍来识别(参见诊断标准)。这种对错误的关注意味着自闭症的优势被系统地忽视了。这篇文章并不否认自闭症可能很难忍受,但它关注的是自闭症性格的好处,而不是它可能导致所有相关问题。对功能障碍和疾病标签的强调已经引发了公众对“治愈”的期望。认为这是对自闭症的根本误解的想法支撑了这篇文章。
當然,我們需要與這些很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年輕人聯繫起來,當然,我們需要給他們機會,與我們一起在一個共享的世界中體驗和繁榮。但是没有疾病可以治愈 – 而是有一种存在,思考和感知的方式来适应。即使是所谓的“严重残疾状况”也不是一种疾病 –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他们是谁。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世界可能会失去自闭症倾向的独特专注和承诺;世界有可能消灭人类多样性中一条重要而富有成效的链条。一艘优生压路机正朝着那些非典型的颠簸前进。
Lorna Wing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闭症中的“损伤三元组”,她指出[1]三元组不足以作为明确挑选人类的工具,并且多维模型对于处理实际多样性至关重要。 一个类别至少由两个维度标识 – 原则上两个维度足以标识矩阵上的位置。但现实和有效的思考都需要更多。
如果你把任何东西纯粹看作是一个类别成员,那么 事实上 你就会忽略其他可以区分它的维度——例如,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当前位置,或者它的因果历史,或者它的颜色,或者它从特定角度看时以特定方式闪耀的事实。可以说,文化上的一致性——通常被认为是“常识”——与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由相互忽视组成的。在自闭症的文化认同方面,这种无知的阴谋具有严重的实际后果。
一旦语言被纳入我们的早期学习过程,它就会将其绝对的命令强加给我们的思维,而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相信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轻描淡写地说:“言语是心灵的女仆”。他们在文化忽视的阴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有一些常用的词来描述自闭症,这些词非常适合唤起公众放弃大笔金钱的意愿:像“疾病”,“瘟疫”,“癌症”和“流行病”这样的词,像“基因决定的严重残疾状况”这样的短语。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抹去这种恐怖一定是一件好事!难怪自闭症患者有时会觉得他们总是会犯错,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需要适应的世界的心态是由反复肯定的错误假设决定的。本文旨在研究,也许会破坏其中一些假设。
无论自闭症儿童多么困难,无论有时家庭如何难以应对,自闭症并不全是坏事。然而,发现自闭症优势的研究结果一直被忽视或被负面解释。 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实验中,自闭症受试者将更高的准确性解释为“未能应用自上而下的处理”。有关这些典型失真范围的两个信息来源是Mottron 等人, 2006年[2]和心理学教授兼心理科学协会(前身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Morton Gernsbacher的演讲[3],他也是自闭症儿童的母亲。鉴于研究人员是在由充满价值和文化偏见的诊断标准决定的背景下工作的,Mottron,Gernsbacher及其同事暴露的解释性偏见并不奇怪。
应用诊断标准需要对某些行为模式的典型性和可取性做出假设。被认定为自闭症意味着被认定为以越轨的方式做各种越轨的事情。我们如何识别这些行为偏离的典型?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种是明确的主观和充满价值的,“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典型的[尔格很好],这不是……'. 区分典型性与非典型性的另一种方法取决于对统计推导的范数的偏差。在后一种情况下,游戏中的值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尽可能接近正态性钟形曲线的中间是正确和可取的 – 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像其他人一样被认为是可取的。这是一个固有的令人费解的想法。这也与我们从生态学研究中对基本多样性的了解背道而驰 – 物种需要多样性才能长期繁荣和繁荣。彼得·艾伦(Peter Allen)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正式的(但易于理解的)案例,即人类的创造力和探索通过具有不同属性的个体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得到增强[4]。Ballastexistenz的打字机类比几乎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么社会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我房间里的打字机如果完全由螺丝钉制成,没有其他东西,就不会工作。 [5]自闭症中强大的遗传成分表明,当自闭症儿童出生时,自然发生的多样性正在起作用。
诊断标准被载入具有重大权威的文本中[6]。 它们的权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官方的,由专家委员会编写,并且在所有医生中都是标准使用的。反过来,那些专门用于识别自闭症的功能失调或无序的标准,以及识别发生的医学背景,共同鼓励忽视许多维度。
在她的书《 压力下的儿童》(Children under Stress ,1973)中,苏拉·沃尔夫(Sula Wolff)博士有几页是关于自闭症的。她说:“一旦诊断确定,父母和老师发现更容易减少他们对顺从的要求,通过建立孩子的特殊兴趣和才能来教育孩子,并坚持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减少敌意。 [7]这种对诊断角色的人道和乐观的看法意味着人们通常可能会以一种似乎对接收端的年轻人充满敌意的方式执行这些社会要求。
一位有自闭症双胞胎的朋友在他十一岁左右的时候问其中一个:“为什么你们两个在小时候总是逃跑?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是:“因为你恨我们”。 即使我们认为这不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孩子如何区分对他或她的行为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咬和攀爬一切)和对他或她本身的敌意?
“不当行为”在自闭症的描述中往往很重要。这句话假定对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合适的,有明显或广泛持有的态度。无论是对强烈情绪的不自主和不受控制的交流,还是不从标准的表达曲目中汲取的直接沟通尝试,都可能引起负面反应(这是错误的! 这一定是不同的!这些消极反应往往排除了对合法问题和反应的承认或承认;他们倾向于忽视已经致力于沟通过程的努力。这种消极反应无法欣赏友好和善意,无法注意到恐惧,无法识别意义,也无法识别合理的情绪。他们把一切都固定在外表上。谁在这样的交流中表现出同理心的失败?看看这个简短的视频,看看一个非自闭症同理心失败的完美例子,因为行为学家教一个小女孩“如何坐下来”: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425217332743177340 (视频不再在线)
在这里,对遵守社会规范和期望的渴望包括忽视明显的自闭症快乐和玩耍,同样忽视明显的自闭症恐惧。
鉴于自闭症患者对恐惧的广泛报道,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不断受到惊吓,但却继续生活和处理事情的人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无论是否害怕,努力表现以适应往往令人筋疲力尽,并且可能以牺牲其他能力为代价(参见 www.autismandcomputing.org.uk 的单向性讨论和彩色勺子…以及社会规范,其中有一个版本的“勺子理论”,该理论也建立在处理资源供应有限的基础上)。
因此,被照顾者/教育工作者视为社会赋能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是个人残疾。这是关于将自闭症儿童视为有缺陷的,并专注于修复缺陷。
坎纳 等人 (1972)发现,那些被贴上“过于狭隘的利益”或“孤立的痴迷”的东西,往往建立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就业的基础,并与他人建立联系。如果我们认为自闭症中“不均衡的技能状况”和“不寻常的兴趣”本质上是适应不良的,我们可能无法建设性地适应这些差异。我们可能无法给孩子们通过观察、探索和发现来学习的机会,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学习。我们可能无法让他们获得最好的沟通方式,即使口头表达对个人来说显然是费力的,并且由于表达或处理问题而无效,我们也可能坚持使用口语。如果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茁壮成长并融入其中,那么从长远来看,给他们时间和工具来发展,分享和探索他们的兴趣可能会激发成功的沟通,并且比专注于修复他们的行为更有成效。这些很可能是具有强烈而持久的兴趣的孩子,这些兴趣不符合刻板的期望,因此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适合,他们也可能无法适应自己的兴趣。知道你不合群既不足以知道是什么让你变得异常,也不足以让你适应,如果你确实发现了这一点,也不足以让你适应。
“固执”,“固执”,“不合作”,“不顺从”,通常是用来描述所有年龄段的自闭症患者的词语。所有这些话都假设其他人有权告诉你该做什么,而学会做别人告诉你要做的事情是学习的基本要素——有时被称为“学习学习”,但实际上是“学习被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孩子坐下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成就。但这可能不是自闭症儿童学习的最佳方式,当他们有机会为自己学习时,他们可能会做得特别好。 [8] 此外,做其他人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探险家,参见(Allen & McGlade在脚注4中引用),我们需要不墨守成规的人和个人,他们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9]。
学会总是做你被告知的事情会让你不恰当地顺从,并可能成为各种虐待的被动受害者。
无论如何,在一种情况下被称为固执的特征在另一种情况下将被称为承诺,专注,坚定和坚定。有关明显令人钦佩的自闭症坚持和决心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些例子,请参阅Posautive Youtube组中的一些短视频。[10]至于顺从,在我的观察中,当一个人 – 自闭症或非自闭症,儿童或成人 – 能够欣赏任务的意义并被邀请帮助执行该任务时,他们将以善意这样做 – 希望本着合作而不是遵守的精神。
在他们关于他们看到和诊断的儿童的后续报告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Kanner和同事引用了一位雇主对他的自闭症工人所说的话,他说他“非常可靠,可靠,彻底,对同事有思想。 (Kanner, Rodriguez & Ashenden 1972 [11])最近,Hagner和Cooney对十四名“成功就业的自闭症患者”的研究发现“……对自闭症员工的最高评价… 自闭症患者显然在各种各样的社区工作中拥有对商业世界有价值的技能和才能,并且在所研究的工作场所中,大多数人不仅被视为成功,而且被视为杰出的员工。 他们接着说:“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证实对自闭症患者的常见刻板印象,是员工被认为的社交方式。大多数员工与同事有频繁,有意义的互动,并被视为友好和善于交际“,第95-96页(Hagner & Cooney 2005)[12]。
根据记者Ker Than的说法,“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经验比生活更受观察,而支配我们人类行为的情感暗流是无法接近的。 他们通过明确的理论来猜测他人的精神状态,但最终结果是一个没有动机,意图或情感的行动,手势和表达的列表 – 机械和非个人化。 (2005) [13]
我们自然倾向于认为,情绪反应的明显迹象总是符合我们对某些情绪应该如何传达的期望。在缺乏这种“适当”的外在表达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假设缺乏内在感觉。对于那些在社会上可接受的自我展示方面有问题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假设,因为每个被诊断为自闭症的人都必须这样做。
請參閱自閉症作曲家和思想家大衛·安德魯斯(David Andrews)的短片[14]“I Go Down”,以獲得自閉症情緒的一些直接證據。 [15].音乐是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形式。 像许多人一样,他发现音乐是传达感觉的最有说服力的手段。这也是自闭症创造力的直接证据。
我们通过社会规范和期望来判断适当性。例如,在西方,在报道或接收可怕的新闻时,咧嘴大笑在文化上受到强烈反对,但在某些文化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一些自闭症患者发现,在情绪压力下,他们无法控制地表现出A.M.Baggs的兄弟所命名的“死去的仓鼠笑”。以下是Baggs对此的看法:
当我做错了什么,知道它,并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震惊时,我会微笑;当我知道有人在附近死去时,我可能会微笑;在各种紧急情况下,当有人倒下或大量流血时,我会微笑;当我身边的人死去时,我会微笑,包括动物;在自然灾害,战争,种族灭绝和恐怖袭击中,我微笑;我微笑着看着人们互相攻击;我微笑着想着关于人的坏事…我的嘴巴被卡住了,痛苦地,微笑着,或者笑着,我什么也做不了来阻止它……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不快乐,我不觉得这些事情很有趣。 当我坐在那里微笑或大笑时,我的实际感受是强烈的厌恶或恐怖。 这里没有乐趣,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不会使某人成为怪物,那就太好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人类(以及一般的灵长类动物)反应[即“神经质的笑声”),有些人比其他人走得更远。 [16] (我的强调)
自闭症患者经常被指责缺乏同理心。 让我们想想“同理心”的含义和“同情”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同理心的想法在上个世纪过半段的童年中并不多见。它在20世纪60年代从它在治疗环境中的使用进入常用语,特别是通过心理学家和治疗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广泛阅读工作。 根据罗杰斯的说法,同理心是一个“进入他人的私人感知世界并彻底融入其中的过程。 它包括每时每刻都敏感地敏感地对待在这个另一个人身上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感觉意义,对他/她正在经历的恐惧、愤怒、温柔或困惑或其他任何东西。 (罗杰斯, 1980 [17])大多数话语不太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情感深度。在治疗语境之外,“同理心”往往被用来描述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反应 —— 你感觉不好,我感觉不好;你感觉很好,我感觉很好,反之亦然 – 因此我们理解彼此的感受。可以创建友好的个人反馈循环,其中将共同的感受表达为相互认可和肯定。它是关于通过识别同一性来理解他者性。可能,同理心已经变得更加突出并获得这种文化价值,因为社会变化倾向于消除其他(非标志)共同认同感的来源(见鲍曼2005[18])。它也可能是Ballastexistenz博客中讨论的日常生活“疗法”的一部分[19]
慈悲的概念至少与佛教一样长,即大约两千五千年。 慈悲的定义是:希望别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当自闭症患者意识到任何种类的生物(包括人类)的痛苦时,他们往往会发现它难以忍受,并热情地希望它结束,如果可行,将采取措施避免将来造成这种痛苦。为了感受到同情心,有必要体验同理心吗?似乎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除非理解其他生物能够经历痛苦取决于“进入”他们的“私人世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绊倒了我的狗,他大喊大叫,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如果我突然发出声音,我的猫跑开了,我知道他被吓坏了。
当我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感到后悔时,我不会做任何读心术或情绪交换。我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的感受。体验同理心和同情心确实会让一个人感觉非常糟糕。(也许这就是当前“同情疲劳”趋势的根本原因?
无论如何,陪审团仍然对自闭症的同理心持不同情。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得出结论:“尽管这项研究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在认知同理心和心智理论的衡量标准上得分较低,但他们与IRI(移情关注)的一个情感移情量表上的对照组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得分高于另一个对照组(个人痛苦)。 因此,我们建议应该重新审视AS中的同理心问题“(Rogers et al. 2006 [20])。
如果你能够识别自己身上的某种感觉,那么识别另一个人的感受一定更容易。
Ben Shalom和其他人的研究显示,在他们研究的自闭症和非自闭症群体中,对刺激的身体情绪反应处于同一范围内。诊断和非诊断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不太可能报告与可测量的身体感觉相关的感觉。 [21]
有時候,你會從你所聽到的關於自閉症的情況下認為,自閉症患者沒有能力去愛。但大多数爱自闭症儿童或自闭症成年人的人会愉快地学习其他知识,无论这种爱可能表现出非常规[22]。 關懷,希望減少在另一個人面前的任何痛苦,奉獻,承諾和喜悅:這些都是長期愛的構成部分,無論關心的人是否意識到某種特定類型的感受。 [23]
如果同理心涉及“调谐”他人的感受,那么我的观察 – 基于数百小时与各种自闭症成年人在各个明显能力水平上的一对一 – 是自闭症患者确实学会了这样做。 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接受基本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可能在类似的时间尺度上,可能更早,可能更晚。可能是不同积极或消极情绪之间更精细的情感歧视会在比平均水平晚的时候出现,如果有的话。但是,竖起大拇指/竖起大拇指的极性是所有情绪状态的基础,自闭症患者对此并非无动于衷。融入和不融入是关于处于这些社会意义的接收端。自闭症患者不适合,因为我们往往不适应他们,即使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适应我们。 引用迈克·斯坦顿(Mike Stanton)的个人标签:让我们让自闭症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
确认
总的来说,我要感谢我的许多自闭症朋友多年来的耐心和建设性支持。除了那些在正文中工作的人之外,我必须感谢自闭症中心(www.autism-hub.co.uk)的每个人,感谢他们活泼的头脑,努力工作和有效的沟通。我必须单独提到卡米尔·克拉克(Camille Clark)和菲利普·阿什顿(Philip Ashton),因为他们对本文做出了非常有用的研究贡献。塞巴斯蒂安·德恩也值得特别感谢。
引用
- [1] Wing, L (2005) 'Reflections on Open Pandora's Box,'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35, 2, 197-20
- [2] Mottron, L, Dawson, M, Soulières, I, Hubert, B, Burack, J (2006) 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 in Autism: An Update, and Eight Principles of Autistic Perception. 自闭症与发育障碍杂志, 第36卷,第1期,第27-43页(17)
- [3]
http://qtstreamer.doit.wisc.edu/autism/Core%20Deficits_300k.mov - [4] Evolutionary Drive – The Effect of Microscopic Diversity, Error Making, and Noise (pdf) by P.M.Allen and J.M.McGladeEvolutionary Drive – New Understandings of Change in Social-Economic Systems (pdf) by P.M.Allen, M.Strathern, J.S.Baldwin
- [5] http://ballastexistenz.autistics.org/?p=44
- [6] APA (1994)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 第四版,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卫生组织(1992年)。 《国际疾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第10次修订版(ICD-10)。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 [7] 菲利普·阿什顿(Philip Ashton)在“行为主义者的不当行为”讨论板上引用
- [8] 参见 http://www.kevinleitch.co.uk/forum/viewtopic.php?id=15&p=3 的讨论(特别是米歇尔·道森在09-02-06和24-05-06上的贡献)。
- [9] 有关为何参见 www.youtube.com/watch?v=40XpnCqZnhQ 的示例
- [10] www.youtube.com/groups_videos?name=posautive 是整个群体的链接。
- www.youtube.com/watch?v=AxAR9dnSuQM 乌尔维尔
- www.youtube.com/watch?v=hxGsFjticKE 里洛像鱼一样游泳
- www.youtube.com/watch?v=3TIR_hwPZi0 卡西亚内翻滚
- www.youtube.com/watch?v=nNbEG1eZJ0s Runman – “Life”
- www.youtube.com/watch?v=StXFQ8pH2W4 快速学习者的一些抽象动画
- www.youtube.com/watch?v=p6cOp6EDFlI 篮球经理得分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mPZc5oVRA – 自闭症欣赏项目(TAAP)。
- TAAP视频,以及自闭症艺术家拉尔夫·史密斯(Ralph Smith)的作品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mR6WFdWyU 以及Urville和动画,都说明了自闭症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令人愉快的博客网站也是如此:
- http://www.devon.trigmafall.com/
- [11] http://www.neurodiversity.com/library_kanner_1972.html Leo Kanner、Alejandro Rodriguez 和 Barbara Ashenden (1972) 免费提供 自闭症儿童在社会适应方面能走多远? 自闭症与儿童精神分裂症杂志, 2(1):9—33
- [12] 哈格纳, 大卫;Cooney,Bernard F.(2005)“我为每个人做那个”关注自闭症和其他发育障碍,第20卷,第2期,夏季,第91-97(7)页
- [13] http://www.livescience.com/humanbiology/050427_mind_readers.html
- [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bB571g9R8 (这里的年轻人不是自闭症,这只是理想反抗的一个例子)。
- [15]脚注10链接的几个视频也是如此。
- [16] https://ballastexistenz.wordpress.com/?p=189
- [17] 罗杰斯,C(1980)一种存在方式。 霍顿-米夫林,1980年
- 鲍曼,Z(2005)液体生活。 剑桥:政体出版社。 国际标准书号0-7456-3514-8
- [19] https://ballastexistenz.wordpress.com/?p=169
- [20] Rogers K, Dziobek I, Hassenstab J, Wolf OT, Convit A. (2006) Who Cares? 重新审视阿斯伯格综合症中的同理心。 J 自闭症 Dev Disord. 8月 12;[Epub 预印]
- [21] 本·沙洛姆; 莫斯托夫斯基; 黑兹利特; 戈德堡; 兰达; 法兰; 麦克劳德; Hoehn-Saric,R 高功能自闭症儿童正常生理情绪但意识情绪表达的差异,第395-400(6)页
- [22] 对于一些证据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SqCQdePPyY 自闭症的面孔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DrsWPE-3bQ 温迪喜欢鸟类和…
- [23]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Wendy Lawson(2006)Friendships the Aspie way,Jessica Kingsley,伦敦。